
上面这幅图,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讲座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周兴在其研究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成名作《说不可说之神秘》中于结语时所附。按照孙先生的说法,“这个图当然不是海德格尔画的,但大体合乎海德格尔的意思。其情状颇近于玄秘的‘太极’了。由上图可观,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偏执于‘显’处,是‘有’论(‘存在论’)。‘显’处有光、有太阳。哲学、神学、科学都在‘显’的区域中,所以‘光’可以是哲学的理性之光,可以是神学的上帝之光。正因此,海德格尔能够把西方形而上学称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

权威专家孙周兴的研究已经表明古老东方的《易经》思想能与现代西方哲学一哥的玄思遥相契合。有此作虎皮,下文循此路径所进行的进一步阐释就有可能少遭些被固守学术藩篱的严谨之士指斥为江湖野路的批评。
其实,今日之学术藩篱多是由执着于中国问题研究中的西方理论视角而固设。刘笑敢就曾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内的以西释中现象称之为“反向格义”(参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其肇始者,胡适、冯友兰是也。相较于以本土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术语的传统格义,研究性、专业性的“反向格义”则被据为近代学术的话语主流。但问题是,在中西关系开始再平衡,文化自信力正逐渐上升的中国当下,以西释中的“反向格义”是否有必要深刻反省,并敞开足够宽广的胸怀徐徐接纳以中释西的“正向格义”呢?
牢骚之后回归正题。我认为,西方哲学所经历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连同马克思那独辟蹊径的实践论其实是大可以被“广大悉备”的《易经》所“正向格义”的:先天八卦中天地定位即言本体论(乾天坤地为本体),山泽通气即言语言论(兑为说),雷风相薄即言实践论(震为足为行),水火不相射即言认识论(离为火为认知)。下面,我以《易经》的视角来格义一下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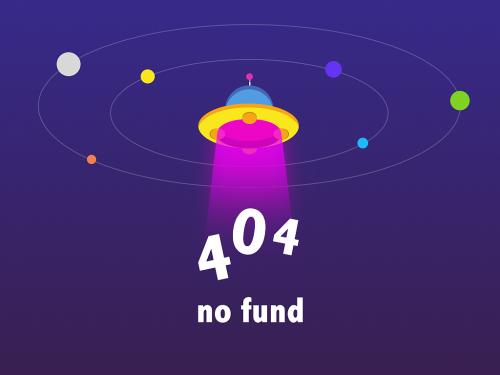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分欧陆的“人文语言哲学”和英美的“分析语言哲学”两路都实现了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超越了语言的科学层面、社会和知识层面的研究而直接深入到“语言-存在”之思。为何语言关乎存在呢?因为天地定位之后,就要山泽通气,气机的流动是万物产生与变化的前提。于人世言,山泽通气的结果是感性人的诞生。人如艮土被抟塑而成,上帝在其鼻孔(艮为鼻)里吹气(兑为嘴为吹),有灵而活。人的存在正是与语言相伴而生,语言(兑说)是人传递气息的工具。

海德格尔深刻之处就在于他能打破人是语言主人的习见而直入道境。他视语言为“大道”的展开,人言植根于道说,道说借人言而发显。不过,海德格尔将道说描述得过于神秘。其实,“大音稀声”的道说实拜海洋(兑为海洋,占地表71%)与陆地(艮为陆地,占地表29%)之间阴阳气流往复运动之所赐。这才是人类语言形成的原始根据,《易经》将之称为泽山咸卦。咸代表无心之感应,表明山海之间的通气是无思无为的自然之应。就人而言,人与天地万物感应道交气息交换,就产生了人言,就产生了“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念念相续。人言的核心是诗,诗的本质为艮(纬书《诗含神雾》云:“诗者,持也。”持者,艮也),诗想抓住什么,就感应来什么言说,因而最丰富无碍。海德格尔认为,通过诗意的命名,诗人创建持存,道说神圣,而人正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盖诗意栖居者,泽山咸象也。
然而道说既显又隐,既澄明又遮蔽,这阴与遮蔽来自于山泽关系的另一面相“山泽损”卦——地表板块的运动会导致海洋的开和闭、山脉的升和降、陆地的汇聚和开裂,因而,“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艮为止,兑为说。假如将泽山咸解为止不住地说,那么山泽损则是止说,止说之境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即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海德格尔认为,合于“逻各斯”的思更具有庇护性和聚集性,更能突入隐匿着的“大道”,深入那神秘的遮蔽中心。盖入思者,山泽损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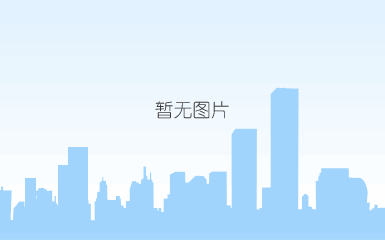
泽山咸与山泽损合之叠成说不可说之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海德格尔曾引用过一首瑞士德语诗人特拉克尔的《冬夜》诗(孙周兴译),似可拟喻之:
冬夜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了盛筵。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下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
在诗中,晚钟、盛宴、金光、面包、美酒等诸兑说之象闪烁于冬夜、雪花、幽暗、寒露、漫游者等不可说的阴藏气息中,其间又杂有房屋、大门、门槛、树等艮象,于是,那神秘的说不可说之境便油然而生。古人词云:“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大概就是此说不可说之境的写照吧。